不知何处是故乡(一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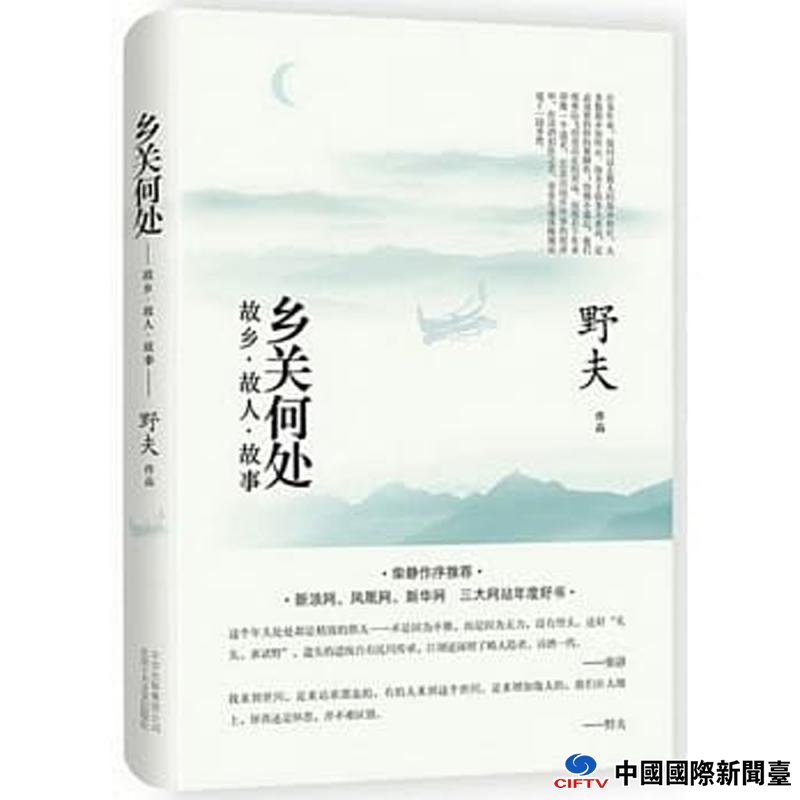
野夫是个土家族的散文作家,我第一次读他的文章是一次旅行中的杂志上看到他署名的散文,字裏行间充满了对人性的深度思考,对人间生老病死带有悲天悯人的感怀,那文字彷彿不是写作,而是一个人的独自沉吟,简简单单的文字,但是处处透出发自心底的呐喊,他的文字有种让人一看便动容落泪的境地,我想这与他的人生坎坷经历或有关係:野夫在1990年脱下警衣入狱,六年的刑期满前,父亲罹患癌症去世,刚出狱母亲为了不给孩子们负担而跳江自杀,这样的经历致使他的文字都带着点点血泪。
这本《乡关何处》(图,网上图片)更是野夫对尘世的一曲輓歌,他从怀念江上的母亲开始,记录了儿时跟随母亲以及外婆在南方生活的苦难岁月,特别是外婆用慈祥的爱意抚慰着他幼小的心灵。儘管这位见识颇深,能诗会画的外婆经历了坎坷的一生,新嫁后遭遇家道中落,稍后由於战乱家人四散,丈夫以为她死於战乱而新娶,外婆因此一人领着女儿回到乡下老宅辛苦操劳,这之后一人担起所有的家庭重担。正是这样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,用她的怀抱给了作者最大的爱与温暖,因此野夫在怀念外婆的文中写道:
“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麼叫做死亡。那年我21岁。在那个秋天,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─外婆─也是一生中给我影响巨深,爱最多的亲人,终於走完了她78年艰难岁月,忽然离我而去了。在那之后的若干年裏,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。”
正是由於幼时外婆给了作者无尽的爱,所以在外婆去世后,野夫按照土家族的丧俗礼仪,在亲人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裏,每到黄昏,都去外婆的坟前送灯─意在为她照亮那漫长的冥路。在寂寞萧条的后山,野夫便独自坐在半山一直到夜色四合,才依依惜别外婆的孤坟,需要这灯光照亮此后人生的路。
野夫的母亲和外婆这两代女性,用了自己的一生给子女带来扶持,儘管性格不同,野夫的母亲同样是用自己瘦弱的一身替家庭阻挡住外界的伤害,但是自身经历了一生的苦难,特别是在晚年为了不给子女造成负担而跳江而亡,使得野夫在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浸满了血泪之痛。
“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,秋水生凉,寒气渐沉。整整十年了,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,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,至今仍暴尸於哪一片月光下……”
野夫的文字似乎都带着泪水,他的散文都面对着大地,正是由这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,字字句句都是由心底的浓烈情感所迸发而出,这本《乡关何处》应可以了却作者的一段乡愁。
儿时的閒情记趣
明清时代出了很多散文大家,特别是生於姑苏城的沈复,更是因《浮生六记》而备受后人推崇,这一本自传体的散文,用了生动的笔触描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,除却我们在少时学堂课文摘选的童年趣事之外,还有众多山水遊记,閒情逸致,与妻子芸娘举案齐眉点点滴滴的爱情婚姻生活。这是一位生性浪漫而温和的文人一生的纪录,悲欢离合,酸甜苦辣都在这笔墨之间传递,最为樸实而诚意的描述,让这部小书,特别是沈复与芸娘生活中的点滴力透纸背,穿过百年的时光,呈现在我们眼前,依旧是那麼鲜活。也难怪林语堂、俞平伯等大家都被此书深深吸引,林语堂也曾为此文做了外文翻译,远播海外。浮生六记原有六卷,如今仅存了四卷,包括童年时期的乐事《閒情记趣》,与芸娘生活中的点滴《闺房乐事》,前期生活安定时遊走山水之间的《浪遊记快》,以及生活中后期的穷困潦倒,流离失所的生活和奔波《坎坷记愁》。
李白的《春夜宴从弟桃李续》中有诗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”沈复的性格就极为相近这“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”的气质,这个生於文人之家的姑苏人,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,一生靠卖画维持生计,中间为生活也曾沦为名不见经传的商人,然而这种恬淡寡欲的性格却将生活中的点滴由笔端,充满灵气展露无余,呈现给我们一个多情多义,热爱生活,在布衣饭菜之中,依旧可乐终身的文人。








